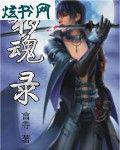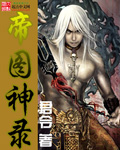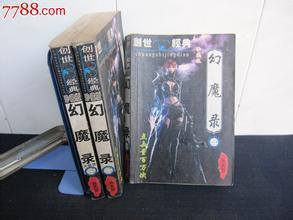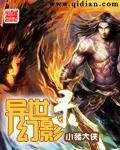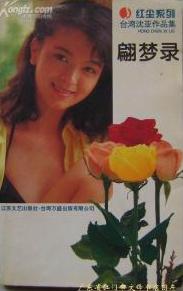五胡烽火录-第157部分
按键盘上方向键 ← 或 → 可快速上下翻页,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,按键盘上方向键 ↑ 可回到本页顶部!
————未阅读完?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!
阳鹜欲言又止,封奕张了张嘴,慕容隽已站了起来,厉声说:“这时候,我们应该在那儿?——在蓟京,在襄城。冉闵已被我们打成残破,可离开了我燕军,石祗那小子连冉闵残军都胜不了。
这本该是我们的好机遇——冉闵无力再战,石祗苟延残喘,我军坐山观虎斗,待石祗灭亡,我军顺势而下,一鼓而取中原。但现在,我强大的燕军竟然窝在辽东边上,呆呆地看着辽东发愣,进亦不能进,退亦不能退。
再这样下去,我鲜卑将失去千载难逢的机遇,我们只能看着棘奴(石勒对冉闵的称呼)战胜石祗那狗儿。此时不进,等姚戈仲、苻健斗出结果,中原之地或归于羌,或归于氐,与我鲜卑何干?”
慕容隽一锤定音,鲜卑贵族急得满嘴燎泡。
是呀!中原,哪里有最温顺的奴隶,有最美的汉家女子,有最结实的房子、有最温暖的冬天,鲜卑不取,被氐族羌族取了,今后,鲜卑人只能在辽东的野地里嚎哭了。
没去过中原不知道,没享受过中原不知道,既然去过、享受过,怎肯再舍弃?现在不取,无论姚戈仲还是苻健占领中原后,鲜卑人花十倍力气,也不见得能再入中原。
“弃辽东,进中原”,鲜卑贵族群情激奋。
慕容恪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,自言自语:“现在,铁弗高在想什么?”
“我什么都没想”,辽东,牛庄码头,高翼面对了一个须发皆白的长者,颇为无赖地强辩说:“全按公式推算的。”
这位须发皆白的长者名叫虞喜,今年六十九了,其父亲虞察是孙吴的征虏将军,曾祖虞翻是三国名人。
虞喜是为了一本汉历与高翼争执的。在这时代,历法是神圣的东西,关系到社稷的正统与传续,它不容任何人篡改,但高翼改了。
打从晋使开始赐历起,高翼就知道他修改历法可能惹来大祸,所以三山的历法被禁止外传,但没想到虞喜还是获得了一份三山万年历——类似现代万年历一样,阳历与阴历共存的三山万年历。
虞族是会稽余姚望族,吴亡以后,因为是前朝旧士族,虞喜一直没有出仕晋朝,待在家乡读书自乐。
会稽临海,过去是吴国水军基地,吴国的水军就是从这里出航辽东并发现台湾岛的。三山与晋通商后,鄞州、钱塘(今杭州)、余姚成了三山商人的主要落脚点。虞喜是在余姚接触到三山商人的,作为世家望族,他不仅与三山商人交往密切,而且还与大食、拂菻、天竺的胡商番僧有过交往。
数月前,一名三山商人在余姚病故,临死前将遗物托付给虞喜,希望他将之安葬于故乡。
本来,这事只要转托给鄞州三山商人,就能完成那人的遗愿。但虞喜翻检那人的遗物时,发现了他珍藏的一本万年历,于是,他坐不住了,不顾年老体衰,坚持北上三山,询问这本万年历的由来。在三山没找到高翼,他便追到了牛庄。
说起虞喜来,那可是个历史大名人,他是中国首位发现岁差,以及首位否决“天圆地方”学说的人。他所著的《安天论》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
所谓岁差是指,地球公转一年不是完整的356日,而是365。2422日,这样,以365天为一年计算,天长日久会给历法造成很大的误差。古人以前不知这个差异存在,直至虞喜才发现了岁差的存在。
虞喜不是第一个发现岁差的人,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比他早发现岁差500年。虞喜也不是当时发现岁差最精确的人,当时最精确的岁差来自于神秘的玛雅历,玛雅人精确计算出太阳年的长度为365。2420日,与现代人测算结果仅误差0。0002日,就是说5000年的误差才仅仅一天。但虞喜是中国发现岁差“第一人”。
虞喜发现岁差,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尤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令人遗憾的是,在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中却没有任何反映。而这一结果也没有运用于天文学,直到百余年后,祖冲之根据岁差做出大明历,才约略记述到虞喜,后人正是根据这一记述,才确定虞喜是中国岁差“第一人”。不过,这些高翼并不知道。
祖冲之做出大明历,起初也不受重视,宋孝武帝刘骏的宠臣戴法兴蛮横地说:“圣人曰:天不变,道亦不变。历法是古代传下来的,不能改动。改动了就是亵渎上天,叛祖离道。”
但祖冲之的儿子有出息,他与当时的梁武帝萧衍关系密切,所以大明历最终得以推行,祖冲之大名也被人知。
科学,与真理无关,只看你儿子与当官的关系好不好。关系不好,你便是祖冲之本人也照样踩你——这就是当时的现实。
虞喜得到的万年历是三山的文化普及版,三山正式的航海历比这个要复杂的多,它来自于海员常用的格里历,其上不仅有太阳历与太阴历的对比,而且还有每日星空图(用于测量纬度经度),潮汐图,等等。
三山的阴阳历对比主要用于航海,它不是用甲子纪年法搞得甲申,戊庚那一套,而是简单的“七月初几”,“八月初几”等记述法。万年历编排了500年历法,不仅有闰月,还有闰日出现。虞喜从这里看到的就是对岁差的修正,所以他赶来三山,进献《安天论》后借机询问高翼为什么如此编历法,当初编撰这本历法是怎么想的?
怎么想的?高翼是根据手头的航海历照猫画虎推算出的历法,他能怎么想,所以只好含糊其辞。
虞喜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:“公式?何谓公式?怎么推算?”
高翼被逼无奈,转守为攻:“那么,你是如何发现岁差的?我不可理解……比如,发现岁差有两种方法,一种是实测法,要356天连续观测,但你不可能有连续运转356天的钟表——即使有这种钟表,现在也不可能精确如斯?你怎么实测出岁差的偏移呢?你甚至连望远镜都没有,怎么观测?
计算法……你怎么计算出来的,你不可能懂几何学,你不可能懂三角函数,你不可能懂二元二次方程解法,你不可能懂万有引力常数……地球是圆的,这你知道,但你知道赤道长度、子午线长度么?这些书籍我这儿正在翻译,你没有这些数据,怎么算出岁差的?”
虞喜平静地回答:“我看的?”
“看的?”高翼惊愕了:“你怎么看出来的?……我可找见组织了,你手机号是多少?QQ号呢?把E…mail地址给我,我给你发邮件!”
高翼后半部分话说得很迅捷,几乎是连珠炮似地脱口而出,但虞喜却似乎冲耳未闻他颤颤巍巍地抖动着白发,说:“古历,尧时冬至日短星昴,今2700年矣,短星昴乃东壁中,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。”
虞喜所说的是,尧在位的时代,依《尧典》所载,冬至日昏中星为昴星,而在虞喜的时代,冬至日,昏中星为“壁9度”。通过冬至昏中星的对比,可得到太阳在恒星间运行一周,差数为每50年退1度(虞喜所说的“度”是黄道度数,解释繁复,此处不再细说),这就是岁差。
“这样也行?”高翼惊得目瞪口呆:“这……这这,这么简单!”
古人的智慧真不简单啊!
可为什么这样明显的差别,我们花了2700年才出了个虞喜,才把看清的事实记录下来?
“书,你刚才说到正在翻译书籍”,虞喜执拗地问:“那些书籍中可有方法,能算出岁差来?”
“当然”,高翼斩钉截铁地说,他眼珠一转,补充说:“计算方法九百年前就有了,你知道喜帕恰斯吗,他在500年前就算出了岁差?想不想看这些书……嗯哪,有代价的,老先生学富五车但年老体衰,我三山有最好的医生,老先生不如在三山住下来,我给你配备最好的医生,先生一边读书,一边教教弟子……怎么样?我给你提供书——你看不完的书,纸、笔、墨、马车、住房……,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,嗯,这里有几所书院,我只要求先生把《安天论》传授给学生,如何?”
“几品官?”虞喜问。
“教授,几品官?”高翼忽起一股莫名的愤怒,答:“教授者,教书育人也,教授要品级何用,‘我们的煤矿很安全’、‘非北京人禁止进入北京’‘索马里人有产权可以,咱中国人具有产权违宪’……?这些不都是那些御用教授说的?
不,我三山‘教授’没有品级,只管教书育人,也不向人收费——行嘛?”
第二卷 艰辛时代 第137章
也许,虞喜早已从那位已故的三山商人口中,听说过汉王有胡言乱语的习惯,所以他对高翼的话采取了“选择性无视”态度,直奔重点地回答:“无品,甚好!书在哪儿?书院何在,领我去?”
这样也行?
高翼长舒一口气。
他不知道,虞喜博学好古,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。西晋帝诏他出任官职,他坚辞。东晋元帝时,诸葛恢任会稽太守,强迫虞喜充任他手下的功曹,对他刺激很大,下决心以后终生不仕。东晋明帝和成帝都多次诏他做官,都被他一一拒绝。所以,教授无品,正和他的口味。
虞喜一生安贫乐道,惟做学问而已。高翼以后人的态度看待虞喜这个真学者,他的担心完全用错了地方。
虞喜并不是平民,虽然他不做官,但身上仍有著作郎、散骑常待等官弦,爵位为平康县侯,与高翼原先的爵位——西安平县侯相等。《安天论》不是一本数学著作,只是一本观点论述的书籍——而且是没有逻辑学作指导的观点论述著作。
虞喜此生主要还是偏重于对经典著作的阐释和训注,他曾“释《毛诗略》,注《孝经》,为《志林》三十篇”。
换句话说,虞喜的学问主要是寻章摘句式的儒生式学问。严格地说,三山不不需要这样经验主义的发现者。但长久以来,学堂事物已耗去了高翼大部分精力,如今学堂内各学科已搭出框架,高翼需要一个类似于虞喜这样,具备发散性思维和严谨治学态度的长者主持教育,以便自己彻底脱开身来,更专注于发展军力。
“高羚,快,用我的马车,送先生去南岭关学堂”,高翼吩咐。
有了这个执拗而专注的老头,想必三山今后的学风会更好……不过,似乎要控制这位老先生寻找摘句的癖好……算了,以后吧——高翼恭敬地送走虞喜,望着马车绝尘而去,他默默盘算。
山那边,慕容恪在想什么?——忽地,高翼的思绪跳到了西方,回身望着奔腾的辽河,他将目光渐渐望向了远处群山。
“时维九月,序属季秋,且逢月圆。暑热尽而柔风清,金叶落而硕果累。俨骖騑于上路,访民情于四野。临帝子之长洲,得仙人之旧馆。舸舰弥津,青雀黄龙之舳……”建康城外郭里,高卉带着两名身躯高大的黑人侍卫漫步秦淮河边,她边走边读着手上的一卷文稿。身后,孙绰一步不拉地跟在后面。
“这个……我不好评价”,高卉咬着手指头,脸上显出努力沉思的形象:“若要我说,我会说:此文灿若披锦,令人读之如饮甘泉。可要我郎君读了,他会说……”
“怎讲?”孙绰急切地问。
“他会说——废话太多!比如:‘时维九月,序属季秋,且逢月圆’,不就是‘九月十五’吗,干嘛兜那么大的圈子,你这通篇文章,不就是说:九月十五,你到白鹭洲玩了一趟,那里风景很好。”
“完了?”,孙绰不甘心地问。
“完了!”高卉想了一想,又咬着指头说:“嗯,若是我郎君手